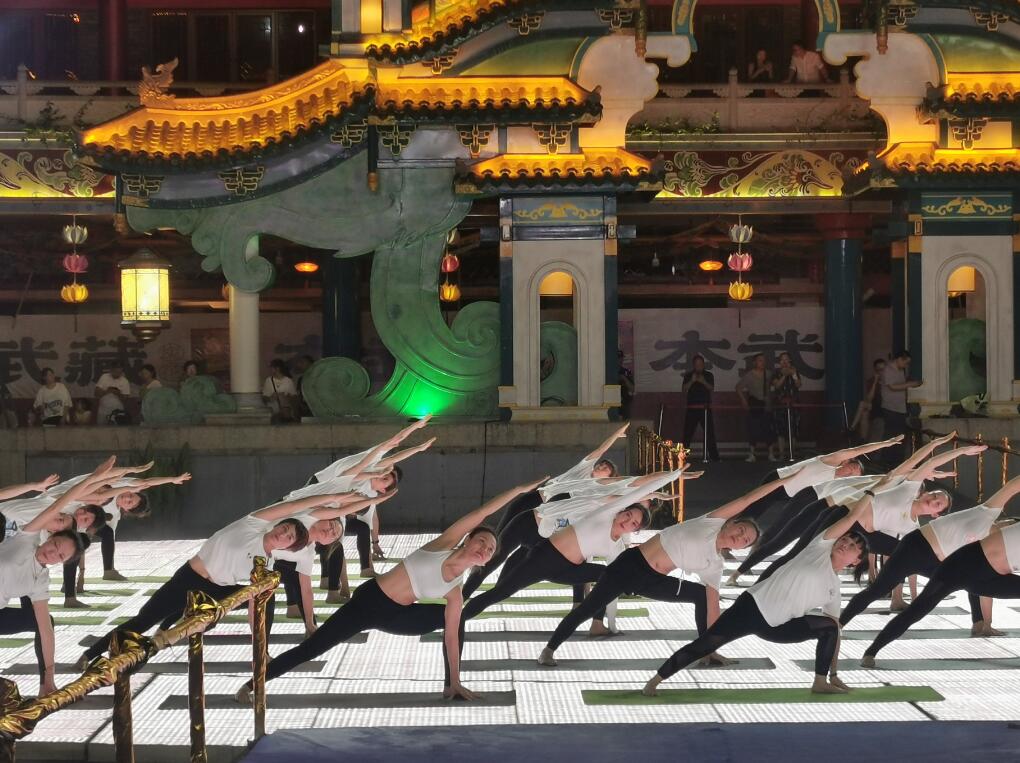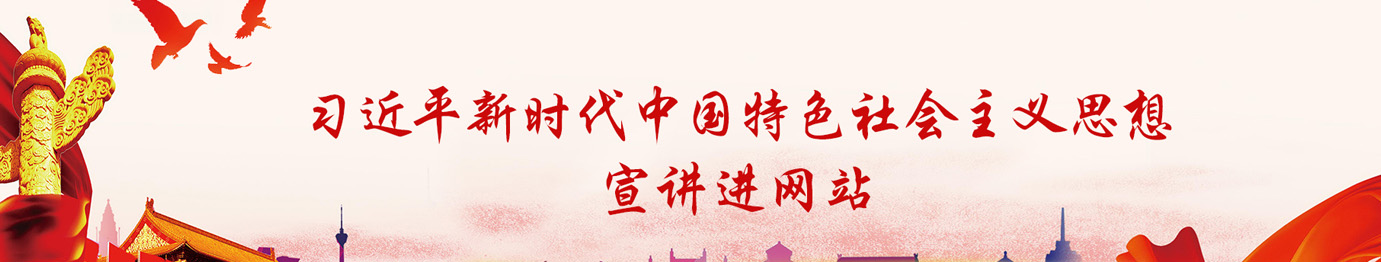三代、四人、三尺情!
新聞來源:眉山網
更新時間:2020-09-09 17:04:35
責任編輯:羅思源
1951年,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及師范教育會議召開后,廣大鄉村掀起了辦學熱潮,外婆徐玉枝經過培訓站上了講臺,成為第一代鄉村教師。
1979年,父親王洪洲以全縣第2名的成績考入眉山師范普師專業。三年后,回到楊場鎮原代安村小,開始執教生涯。
1984年9月,父親王洪洲認識了母親李華琴,兩人喜結連理,一直扎根基層從事教育工作。兩年后,生下女兒王娟。
古井村小、金龍村小、駱壩村小……父母工作多次調動,楊場鎮多個村小都留下了她童年的足跡。2014年9月,王娟畢業后進入仁興小學執教。
外婆從教36年,母親從教35年,父親從教38年,王娟已站上講臺6年……三代人接力傳承,像紅燭一樣,把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奉獻在三尺講臺,照亮了5000多名學生的求知路。
三代、四人、三尺情,超過半個世紀的教育傳承故事仍在繼續……

王娟一家人合影。
第一代教師徐玉枝:50年代踏上講臺
回憶艱苦歲月 白天上課晚上挑糞

9月7日,在丹棱縣城一小區內,83歲的徐玉枝正拿著放大鏡看書。家人說,她年紀大了,很多事情都不記得了。但問及她當年教書的情景,老人家的記憶卻逐漸清晰起來。“1955年,村上派我去夾江師范學習,1956年7月,回來就在丹棱何場中心校教書。"

徐玉枝用放大鏡看書。
50年代初期,舉國上下百廢待興,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及師范教育會議召開后,廣大鄉村掀起了辦學熱潮,徐玉枝等一批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經過培訓成為鄉村教師。
“我19歲開始教書,一個人包一個班,語文、數學、勞動,體育什么課都要上。”徐玉枝回憶道, 那個年代,雖然物質條件艱苦,但大家都是一腔熱血——白天上課,晚上加班挑糞澆菜,有時候上午上半天,下午就要上山砍柴。農村很窮,學生出來讀書不容易, 班上的孩子,無論成績好壞,她都帶著手電筒,翻山越嶺去逐一家訪。“有時候遇到特別偏僻的山路,我就一邊走一大聲唱歌給自己壯膽。”
1979年,徐玉枝調到了楊場鎮徐壩小學任教。“一周上6天課,我住在學校,周日休息一天就回家。”徐玉枝說,當時一個月工資20元錢,家里買不起手表,又擔心上課遲到,每次從學校返家都要背著鐘回來,第二天一早又背著鐘返校。"早上5點多起床,煮早飯,喂孩子,收拾完畢,一根背條把娃兒背上就出發,不管大風大雨,都要按時抵達學校。
那時候,村里都是泥巴路,遇上下雨天,地上的泥濘經過很多人反復踩來踩去,粘性堪比糍粑。徐玉枝記得最清楚的是,有一次連續一個月下雨,穿了一個月的雨鞋,好幾次,腳陷在泥濘里,使勁一提,鞋子都扯爛了。“條件艱苦,也有娛樂。”師生們最期待的,就是學校操場放電影。就像過節一樣,熱鬧得很,多遠的學生都來看,老師還幫學生扎火把,讓他們看完電影打著回家。
從五一村小到金龍村小、徐壩村小……徐玉枝一生都專注在鄉村教育上。19歲踏上講臺,到55歲退休,36年的時間,她教過的學生上千人。在她的影響下,她的女兒李華琴、孫女王娟都成了丹棱的鄉村教師。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長河里,一家人用接力棒似的方式,詮釋著教育工作者的情懷。
第二代教師王洪洲夫妻: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從教
身處偏遠農村 見證教育環境大變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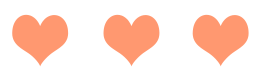
“琴!我走了哈,下午你要記得去接孫孫兒哦。”9月7日清晨7時,丹棱縣楊場鎮中心小學老師王洪洲同往常一樣,與退休的妻子李華琴道別后,斜跨肩包,騎上摩托車出了門。“早點去學校,去守一下學生娃娃們晨讀。”
今年57歲的王洪洲,1979年參加考試,當年他以全縣第2名的成績考入眉山師范普師專業。1982年,年僅19歲的王洪洲畢業后回到楊場鎮原代安村小,成為一名鄉村老師。38年來,他一直扎根基層,先后在楊場鎮原代安村小、徐壩村小、駱壩村小、金龍村小、古井村小等地任教。

王洪洲正在備課。
“當時村小的環境真的很艱苦,每天早上要步行近10公里山路到達學校。每個年級實行‘包班制’,語文、數學、體育、美術等科目都由一個老師上,而且每天5節課,學生和老師中午都不吃飯,一直到下午2點放學。”王洪洲回憶說,“教室全是泥坯土墻房、地面到處坑坑洼洼、窗戶全是白紙糊的……遇到下雨時,外面下大雨,室內下小雨。”
正值改革開放初期,村里很多有知識、有文化的青年,都選擇了到沿海地區去務工。盡管條件很艱苦,但王洪洲從未有過放棄的念頭。“我能考上師范,成為‘科班兒’老師,全靠我們村里的老師和鄰居們的悉心教導。我要是再走了,也對不起父老鄉親們的期望。”
1984年9月,王洪洲認識了同在楊場鎮任教的村小老師李華琴,兩人都是鄉村教師,在進一步了解后,互生好感。“華琴出生教育世家,她的母親徐玉枝老師一直在我們楊場這一片教書。華琴是1979年初中畢業的,后來被安排工作,也在楊場鎮境內的多所村小教書,所以我一開始就很仰慕他們一家人。”而后兩人喜結連理,并一直扎根基層從事教育工作。

王洪洲與妻子李華琴。
從大鐵門、小教室到新校舍、現代化教室,從長滿雜草的草地到寬闊的操場、紅色的跑道,從零散的訓練室到先進整齊的裝備……王洪洲夫妻倆見證了丹棱農村教育的發展。“教育的發展是隨著經濟而發展的,尤其農村教育反應了基層翻天覆地的變化。”王洪洲說。
兩年前,李華琴從楊場小學退休,回顧這幾十年的教育生涯,她感觸很深。“從事基層教育雖然很苦很累,但每當看到山里的孩子們,通過刻苦學習,最終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,我就覺得這輩子真的是值得的。”

王洪洲正在講課。
“華琴是退休了,我還有兩年多,我給學校領導一直的表態就是:只要我還在崗一天,我的課一節都不會缺席,我也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教育好我的每一位學生,站好最后一班崗,將這一屆學生送達彼岸。”王洪洲說。
第三代教師王娟: 2014年成為老師
從小耳濡目染 “長大后我就成了你!”

“清早聽到公雞叫,推開窗門迎接晨曦到……”9月7日,丹棱縣中隆小學教學樓2樓,一陣悅耳的鋼琴聲伴著整齊的童聲飄出教室,音樂教師王娟正一邊彈琴一邊帶領孩子們唱歌。今年34歲的王娟,從小在教師家庭長大,對鄉村校園有一種特殊的情感。
“小時候,教師辦公室是我待得最多的地方。”那時候,王娟的父母在楊場鎮的各鄉村小學教書,2歲的王娟就跟著輾轉,古井村小、金龍村小、駱壩村小等地,都留下了她童年的足跡。在王娟的記憶里,白天父母都圍著學生忙碌,晚上夫妻二人挑燈批改作業,很少有功夫輔導自己。后來恰好讀到了父親所教的班,也沒有受到特別的“照顧”。“他對所有的孩子都一視同仁,我和同學發生矛盾,父親還會先批評我。"
家里的教案和書架成了王娟探索知識奧秘的“第一扇門”。她時常偷偷地拿著教案站在小凳子上,一板一眼地學父母教書。漸漸的,一顆小火種埋進了王娟心中。升學考試時,王娟毫不猶豫填報了樂山師范學院音樂專業。“當時只有一個念頭,和爸爸媽媽一起繼承外婆的衣缽,繼續教書育人。”王娟說,至今她都不后悔這一選擇。
2014年9月,王娟畢業后進入仁興小學執教,后又調至中隆小學。與外婆和父母輩的“包班”不同,現在學校早已經實行分科制,根據所學專業,王娟成了一名音樂教師。
“80年代鄉村小學上音樂課,就是教孩子唱歌跳舞,到我們這一代,內容就豐富多了。”王娟說,現在上音樂課,不僅要帶孩子們欣賞優美的音樂作品,認識體驗馬頭琴、長管等中外樂器,還要教基本的樂理知識,掌握音樂的旋律、節奏。

王娟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。
知識更豐富了,教具變化也很大。80年代,王娟的爸爸媽媽經常到處找掛圖之類的,制作展示教具。而現在,網上電子資源很豐富。“只要花點功夫,就能結合教材制作成精美的PPT,用教室里的投影儀一放,既直觀又全面,學生理解起來更直觀。
過去教師的生活條件很艱苦,大家都住在學校簡陋的公房里。到了王娟這一代,基本都在城里安了家。每天早上6點,王娟起床收拾好,就騎著摩托車從丹棱縣城出發,不到30分鐘就抵達學校。她除了擔任三個年級的音樂教師外,還是一個班的班主任,同時兼任學校德育主任、少先隊輔導員,每周負責策劃安排學校活動等。每天工作繁雜,等王娟把所有事情處理完,往往下班就已經下午6點多了。
教材、教具在變,責任傳承不變。一天10多小時花在學校里,王娟基本沒時間照看自己的兩個孩子。有時候遇到調皮的學生屢教不改,王娟十分頭痛,飯桌上提起,家里幾位老教師紛紛“不吝賜教”——“對這樣的學生,要有耐心。”“當老師,必須要真正吃得苦”,在大家七嘴八舌的鼓勵安慰中,王娟很快又“滿血復活”起來。

記者手記

在堅守與傳承中,我們看到了這個教育家庭,雖然每個人都身處不同年代,但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職業理想:做一名平凡的老師。 也許對他們而言,教師不是一種職業,而是已經滲入他們生活的基因,延續著幾代人對教育的熱愛和執著。
王娟的外婆從教36年,母親從教35年,父親從教38年,而王娟從教已6年……三代人接力傳承,像紅燭一樣,把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奉獻在三尺講臺,照亮了5000多名學生的求知路。
現如今,隨著鎮上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,王娟與父親的肩上又多了一份責任——要讓留守娃健康成長。“隨著鄉村學校條件顯著改善、教育公平不斷推進,每一位留守兒童都可以通過努力完成‘逆襲’。”王娟說,“我們要做的就是用關愛點燃了他們的夢想,釋放了他們身上所蘊藏的巨大潛能,讓他們仰望星空,并且愿意為了星空之夢而腳踏實地奮斗。”
三代、四人、三尺情,教育的傳承絕不止三代,還會有更多的人投身教育,用堅守讓教育更有溫度、更具色彩。
扎根基層育桃李,初心不改譜芳華。在我市,還有成千上萬名教師扎根基層、默默付出。教師節來臨之際,讓我們由衷的道一聲:老師,你辛苦了,節日快樂!愿你們在莘莘學子的深情祝福里,回憶起教育生涯中點點滴滴的美好;愿你們在“尊師重教”的暖風吹拂中,感悟人生價值,增添執教熱情和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