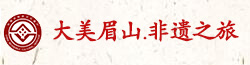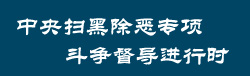蘇東坡究竟懂不懂音律?
新聞來源:眉山網(wǎng)
更新時間:2019-10-27 11:17:40
責(zé)任編輯:羅思源
眉山網(wǎng)記者 陳甜
在歷史上,對蘇軾是否懂音樂有一些爭論。宋代女詞人李清照,寫有影響深遠的《論詞》一文。在《論詞》中,李清照力主要嚴格區(qū)分詞與詩的界限。她公開批評蘇軾的詞是“句讀不葺之詩”,也就是句子長短不齊、湊合在一起的詩句而已。言外之意,這類不符合音律的詞,算不上詞的正宗和上品。于是進入南宋以來,社會上就有蘇軾不懂音樂、不會唱歌的普遍說法。
但南宋大詩人陸游卻不這么認為,他的《老學(xué)庵筆記》記載:“世言東坡不能歌,故所作東府詞多不協(xié)。晁以道謂:‘紹圣初,與東坡別于汴上。東坡酒酣,自歌《古陽關(guān)》’,則公非不能歌,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。”
也許蘇東坡唱得好不好很難考證,但是在音樂方面他也確實是個懂行的人。
東坡醉月。(資料圖片)
出生古琴世家
從小接受音樂熏陶
蘇軾的父親蘇洵,酷愛經(jīng)籍和古琴藝術(shù),是當(dāng)時一位較有影響的音樂鑒賞家和音樂愛好者。《歷代琴人傳》引張右兗《琴經(jīng)·大雅嗣音》:“古人多以琴世其家,最著名眉山三蘇。”少年的蘇軾,對音樂有極濃厚的興趣,三蘇都是彈琴的能手,父親蘇洵琴技最高,家中還珍藏了著名的唐代“雷琴”。
由于從孩童時就受父親演奏古琴的熏陶,蘇軾一生對古琴有著特殊愛好。
為了研究古琴的發(fā)聲原理及特點,他不惜把自己家中珍藏的唐代名貴“雷琴”拆開來觀察、分析其奧妙。為此他還專門撰寫了《家藏雷琴》一文。蘇軾的這張?zhí)拼徘伲倜娌紳M蛇蚹紋,上孔里(龍池處)寫著“開元十年造,雅州靈關(guān)村”,下孔里(鳳沼處)寫著“雷家記八日合”。“岳”也叫“岳山”,它的制作恰到好處,是一張好琴的標志之一,當(dāng)時只有唐代雷氏家族制作的“雷琴”才具有這樣的優(yōu)點。
另外他還發(fā)現(xiàn)琴的聲音是從孔對面的木頭稍微隆起,好像薤菜葉的形狀處發(fā)出,由于聲音的出口處很狹窄不能馬上出去,留在琴內(nèi)徘徊成余韻,這就是雷琴的奧妙之所在。為此蘇軾作詩贊曰:“我有鳳鳴枝,背作蛇蚹紋。月明委靜照,心清得奇聞。”(《次韻奉和錢穆父、蔣穎叔、王仲至詩四首,見和西湖月下聽琴》)
除此之外,他還很贊賞名士李委的吹笛藝術(shù),說:“嘹然有穿云裂石之聲。”蘇軾對所吹的《鶴南飛》曲頗為知音,竟連曲中帶有西北邊疆少數(shù)民族風(fēng)情的音調(diào),都聽得十分清楚。曲終,他贈詩一首,題《李委吹笛》:“山頭孤鶴向南飛,載我南游到九嶷。下界何人也吹笛,可憐時復(fù)犯龜茲。”
嘉祐四年,父子三人進京時,蘇軾在船上細心凝聽父親所彈的琴曲,產(chǎn)生了許多感受,寫出了《舟中聽大人彈琴》一詩:“彈琴江浦夜漏水,斂衽竊聽獨激昂。風(fēng)松瀑布已清絕,更愛玉佩聲瑯珰。自從鄭衛(wèi)亂雅樂,古器殘缺世已忘。千家寥落獨琴在,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。世人不容獨反古,強以新曲求鏗鏘。微音淡弄忽變轉(zhuǎn),數(shù)聲浮脆如笙簧。無情枯木今尚爾,何況古意墮渺茫。江空月出人響絕,夜闌更請彈文王。”
蘇洵撫琴雕塑。眉山網(wǎng)記者 向哲 攝
陽關(guān)三疊還是陽關(guān)四疊
蘇軾給出了正確答案
對于音樂,蘇軾因為感興趣,所以愿意花時間去鉆研。
《陽關(guān)三疊》是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?shù)墓徘倜置蛾栮P(guān)曲》《渭城曲》。該曲是唐時,根據(jù)詩佛王維名作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譜寫而成的:“渭城朝雨浥輕塵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,西出陽關(guān)無故人。”
這首曲子在唐代便廣為流傳,時人以琴聲為伴,吟唱王維詩作。然而,曲譜早已失傳,關(guān)于唐代時這首詩歌具體如何“三疊”的演唱形式就成了一個謎。但是,盡管唐代曲譜缺失,這一曲《陽關(guān)三疊》卻一直在世間傳唱,歷代不衰。歷代文人都對這“三疊”究竟是如何“疊”的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在宋代也有“四疊陽關(guān)”的說法,如賀鑄《采桑子》中寫道:“東亭南館逢迎地,幾醉紅裙。凄怨臨分。四疊陽關(guān)忍淚聞。”
那么問題來了,這《陽關(guān)曲》到底該是“三疊”還是“四疊”,熱愛音樂的蘇軾,專門對其進行了考證。
據(jù)東坡先生本人記載,宋時,人們唱《陽關(guān)三疊》,往往把全詩的四句都作疊唱,但這樣一來,就應(yīng)是“四疊”。如果把每句都疊唱三遍來迎合“三疊”之說,更是雜亂且不合音律。蘇軾任密州太守時,曾偶然在一位同僚那里聽到了古本的《陽關(guān)曲》,聲調(diào)宛轉(zhuǎn)凄涼,和先前常聽到的不同。這曲子除了第一句不疊,每句皆再唱,這才知道古本的“三疊”是這個意思。
后來蘇軾居黃州時,首次讀到唐代詩人白居易的《對酒詩五首》,其中有“相逢且莫推辭醉,聽唱陽關(guān)第四聲”,恰好證明了他的觀點。既然是對酒詩,根據(jù)前后文關(guān)系,“聽唱陽關(guān)第四聲”,指的應(yīng)是《陽關(guān)曲》中“勸君更盡一杯酒”一句。蘇軾表示,用這個來檢驗,如果每句都作疊唱的話,則“勸君更盡一杯酒”應(yīng)是第五聲,白居易明確說是第四聲,那么就可以確定唐時第一句是不疊的。
這個故事,被清人陳廷敬收錄于當(dāng)時的權(quán)威著作《欽定詞譜·卷一·陽關(guān)曲》中,以表示對東坡先生的肯定。由此可見,唯因東坡先生熱愛音樂且精通樂律,才能對《陽關(guān)三疊》有如此精確的考證。
古琴藝術(shù)在封建社會里備受儒家推崇,被其看作是雅、正音樂的代表和禮樂觀的象征。傳統(tǒng)儒家文人們把古琴與琵琶、古箏等樂器區(qū)分對待,認為琵琶、箏是民間演奏“鄭衛(wèi)之音”的樂器,不足以登大雅之堂。可蘇軾卻不這樣認為,他在《雜書琴事》十三則的一則中談到,現(xiàn)在的古琴已被士大夫們看作是“雅正之樂”了,可在周代古琴卻是演奏“鄭衛(wèi)之音”的樂器。現(xiàn)在我們說它是雅器,可它在古時也是一件民間樂器,和現(xiàn)在流行的琵琶、古箏沒有什么兩樣,由此可以看出蘇軾的獨立見解。
雅俗共賞的填詞能手
寫下傳唱千古的好詞
除了喜歡聽音樂,蘇軾還是個填詞能手。
蘇軾二十三歲那年路過忠州(今四川忠縣),就依據(jù)當(dāng)時流行在巴東荊楚一帶的民歌《竹枝》寫過若干首歌詞。他在詞前的小序里提到這種歌曲之所以“幽怨惻恒,若有所深悲者”,是由于前人“傷二妃而哀屈原,思懷王而憐項羽”的緣故。因之他所寫的這些竹枝詞,也就基于這樣的內(nèi)容和應(yīng)當(dāng)具有的風(fēng)格:水濱擊鼓何喧闐,相將扣水求屈原。屈原已死今千載,滿船哀唱似當(dāng)年。
后來他到杭州時,游覽九仙山,耳聞吳越地區(qū)的兒童民歌《陽上花》,具有“含思宛轉(zhuǎn),聽之凄然”的藝術(shù)感染力。但他覺得原來的那些歌詞還不夠理想,于是予以加工潤色,另配新詞:陌上花開蝴蝶飛,江山猶是昔人非。遺民幾度垂垂老,游女長歌緩緩歸……這些新詞因其帶有民間歌謠樸質(zhì)清麗和好唱易記的特點,廣為人們喜愛和傳誦。
值得一提的是,蘇軾還樂于將農(nóng)器使用方法寫成歌詞,便于百姓理解并且推廣。
據(jù)史料記載,蘇軾于宋元豐年間謫居黃州,在武昌的畦田里“見農(nóng)夫皆騎秧馬”,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。他經(jīng)仔細觀察發(fā)現(xiàn),秧馬“以榆棗為腹”(易滑行),“以楸桐為背”(體輕),首尾翹起,中間凹進,形似小船,農(nóng)民騎在秧馬上拔秧,“雀躍于泥中”“日行千畦”。較之過去彎腰弓背地勞作,相差懸殊,真是輕快自如多了。秧馬的另一作用是“系束藁其首以縛秧”,就是把束草放在前頭用來捆扎秧苗,極為便利。
蘇軾對秧馬倍加贊賞,每到一地即宣傳推廣。宋紹圣元年(1094),蘇軾又貶惠州(今廣東惠州市),南下途徑廬陵(今江西泰和),遇見《禾譜》撰者曾安止。蘇軾稱其著作“文既溫雅,事亦詳實”,然惜其不錄農(nóng)器,遂作《秧馬歌》相贈,并附其書后。該詩對秧馬的形制及作用歌詠甚詳。后人還將《秧馬歌》刻成石碑(現(xiàn)藏于泰和縣博物館),使其流傳久遠。正如后來陸游有詩說:“一篇秧馬傳海內(nèi),農(nóng)器名數(shù)方萌芽。”
蘇東坡擅音律,且詞填得極好,無數(shù)文人雅士紛紛上門求詞,一時傳為佳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