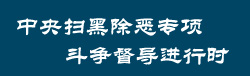在成都遇見蘇東坡
新聞來源:眉山網
更新時間:2019-05-05 10:06:58
責任編輯:羅思源
吳曉斌 文/圖
玉宇路上的蘇軾雕像。
“峨眉山西雪千里,北望成都如井底。”蘇東坡一句話扯出峨眉山和成都的關系。
今年的“青年節”連著“五一”小假,當城里的人們涌向峨眉山的時候,我卻來到比平日空曠許多的成都,漫步城西清水河畔,徜徉城東塔子山旁,尋訪眉山先賢的足跡,與青年東坡傾心交談。
嚴格地說,那時“東坡”之號尚未加身,我遇見的只能叫蘇軾。
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,在詩、詞、文、書、畫等方面都是一等一的高峰。蘇軾之于成都,也成了一個文化地標。
瑞聯路上紀念蘇軾的訪亭。
蘇軾 游成都
蘇軾與成都,只有青年時期短短幾次交集。但梳理蘇軾的成都情結,卻貫穿他自成江海的一生。
蘇軾從七歲起就向往著成都,直到二十歲才實地踏訪;二十三歲為成都知府上書建言;二十九歲返川,在成都會友講學,捐資修橋;六十五歲獲準“赴朝奉郎”,提舉“成都玉局觀”。眼看就要實現與成都的圓滿,然而回川途中病逝常州,先生再也回不來了……
在《洞仙歌并序》的小序中,蘇軾寫道:“余七歲時,見眉州老尼……年九十歲。自言常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……”這首詞作于蘇軾謫居黃州之時,四十年后蘇軾仍然清晰地記得老尼講的故事,可見蜀宮的美景,給年幼的蘇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宋仁宗至和二年(1055),年近二十的蘇軾才第一次有機會游歷成都,在父親蘇洵帶領下與弟弟蘇轍拜見成都知州張方平。張方平初見二子,即視為奇才,“待以國士”,并向翰林學士歐陽修寫了推薦信。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可謂具有歷史性意義。
東坡大道。
成都之行,讓年輕的蘇軾眼界大開。父子三人更是彼此唱和,佳作頻出,后收入《南行記》。
果然,張方平的眼光是獨到的。第二年蘇家三父子進京,蘇軾憑借一篇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拿了個全國第二。若非歐陽修以為是自己門生答卷鬧了個避嫌的“烏龍”,蘇軾就是妥妥的第一。蘇洵、蘇轍也文采飛揚,三蘇一夜間名動京師。
然而,父子三人還沒開始大展拳腳,家鄉就傳來噩耗,蘇軾的母親程夫人因病去世。他們立即放下一切,回到眉山奔喪。
蘇軾服母喪居家時,發生了一件事,展露了他的政治才華。嘉祐四年(1059)春,龍圖閣學士王素自定州移知成都,蘇軾久仰其名,懷著極大的熱情上書《上知府王龍圖書》,為百姓陳情。主要內容是關于如何治理蜀地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。他認為“國家著兵以衛民,而賦民以養兵,此二者,不可以有所厚薄也。”并表明當時“負罪居喪”,不能登門參拜。最終這些意見王素是否采納,不得而知,但后來居民為王素“畫像祠之”。從百姓的反應來看,蘇軾的建議應該起了積極作用。
6年后,二十九歲的蘇軾再次回川,已是“判登聞鼓院,直史館”之職,類似于主管國家信訪辦兼文史館工作。雖然得來有些波折,但至少算年輕的“正處級”干部了。
宋英宗治平三年(1066),蘇軾的父親蘇洵去世。蘇軾強忍悲痛,與弟弟蘇轍送父親喪歸眉山,并居喪三年。
這是蘇軾最后一次回到四川。其間,又訪游成都,遇江水,寄住成都西郊清水河畔“悅來客棧”。這里風景雅致,世風崇文。蘇軾曾在大樹下座談會友,舉酒賦詩,并為當地士子講學。臨走時,還自掏腰包在清水河修了一座青石拱橋。后世人們將這座橋取名為“蘇坡橋”,會友講學的涼亭命名為“東坡亭”,以紀念蘇軾。今天,蘇坡橋已經變成一座漂亮又蘊含深厚文化底蘊的立交橋,橋下精心打造了川劇長廊,成為文化加經濟的大動脈。
除了清水河畔,還有一個地方是蘇軾每次逛成都必定會去的,那就是大慈寺。位于城中的大慈寺,始建于唐肅宗至德年間,堪稱“震旦第一叢林”,距今已有1600多年歷史。蘇軾每到成都必去,不僅僅是對文化名勝之地的追尋,更重要的是該寺六世主持寶月大師就是蘇軾的同宗兄弟蘇惟簡。兄弟情深,讓蘇軾對大慈寺有了特殊的感情。
佇立于成都城中步行街的蘇軾書法。
蘇軾 寫成都
文人喜歡一個地方,總會為之舞文弄墨。
蘇軾寫成都的詩文不少,有的詩開篇直點成都:“忘卻成都來十載,因君未免思量。”“乘槎歸去,成都何在?”“成都畫手開十眉,橫云卻月爭新奇。”……有的詩更是直接將成都入題:《次許沖元韻送成都高士敦鈐轄》《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》《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》《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》……蘇軾對成都的喜愛,一言以蔽之:“成都,西南大都會也。”
“忘卻成都來十載,因君未免思量。憑將清淚灑江陽。故山知好在,孤客自悲涼。坐上別愁君未見,歸來欲斷無腸。殷勤且更盡離觴。此身如傳舍,何處是吾鄉。”蘇軾這首《臨江仙》,表達了一代文豪對亡妻和對成都的深切眷戀。
公元1065年,蘇軾的妻子王弗病逝。從妻子歸葬眉山至妻弟王緘到錢塘看望蘇軾,其間相隔正“十載”。這十年已經客居錢塘的蘇軾沒有一年不想念王弗,不想念成都。可是他卻說本來已經忘記了,因為你的到來又想起,這是蘇軾笑中帶淚的苦痛。大凡人之至情,越是想要忘記,越是揮之不去,成了“難以忘卻的紀念”。
王緘此來,蘇軾得知“故山好”,略感寬慰,悲涼的情感多了幾分暖意。然妻弟短短幾日又要匆匆離去,作者情不能自已,孤客悲涼,別愁斷腸,沒有比這更慘的了。慘到深處,就是徹悟。
“忘卻成都”,其實是不能忘卻。
因為寶月大師,蘇軾對成都大慈寺有一份特別的觀照,并為大慈寺留下不少著述墨寶。他在《勝相院經藏記》一文中寫道:“蜀成都大圣慈寺,故中和院,賜名勝相。”
其時大慈寺內藏唐畫家盧欏伽筆跡以及唐僖宗皇帝與從官文武75人畫像,皆為畫中珍品。蘇軾贊賞有加,觀賞后題名:“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,眉陽蘇軾與弟轍來觀盧欏伽筆跡”,并寫下四個大字:“精妙冠世”。如今這四個鎏金大字立壁佇于成都繁華步行街,注視著世界各地南來北往的游人。
宋神宗元豐三年(1080),蘇軾被貶謫黃州。遭“烏臺詩案”大難,親友多疏遠,而寶月大師卻派人前去探望,并希望蘇軾為大慈寺“大寶藏”作記。蘇軾回書云:“屢要《經藏碑》。本以近日斷作文字,不欲作。既來書叮嚀,遂與作得寄去。”宋紹圣二年(1095),寶月大師圓寂,葬于城東塔子山,蘇軾悲戚作《寶月塔銘》。
成都街頭的東坡元素。
成都 讀東坡
當年的塔子山大概沒想到,除了寶月大師與蘇軾的關聯,千年后,塔子山公園還出了一件與蘇東坡有關的文化盛事。
2003年,在成都塔子山公園相繼出土了三蘇殘碑三通,即蘇軾《中山松醪賦》、蘇洵《提舉監臣帖》和蘇轍《雪甚帖》,掀起了成都乃至全國關注三蘇先賢的又一熱潮。也在這一年,成都塔子山公園與眉山三蘇祠在成都共同舉辦了首屆“東坡文化節”,蘇軾再一次造訪成都。
當年的蘇東坡一定沒想到,千年后,一組以他的名字“蘇東坡”冠名的動車會把成都和他第一次為官的陜西相連。
2018年,“蘇東坡”再次出川入陜,人們可以乘坐“蘇東坡”動車組列車,去看那蘇軾初仕地陜西鳳翔的詩意東湖。也在這一年,成都文殊坊遇上蘇軾,中秋詩樂會蘇軾文化“打卡區”盡享蘇軾詩詞文化的盛宴。
三蘇故事浮雕(其一)。
歷史有幸,后人敬之,現在成都以東坡元素命名的地方為數不少。東坡路、蘇坡路,東坡街道、東坡大道,東坡公園、東坡小學,東坡雕塑、三蘇浮雕……當年蘇軾從成都出發,開始了他波詭云譎的仕途之旅,就再也沒有回來,但我們從這些命名中,依舊可以尋找蘇東坡留下的飛鴻雪泥。
悠悠千載,清水河流淌著東坡先生文韻,塔子山滋養著這一方文風。現在,行走于蘇坡,在東坡街巷,總能碰上幾位低吟淺唱的詩人。
“人不見,數峰青”。蘇軾,東坡,玉局觀,原來你一直都在這里。